在爱的天空下
黄 燕
退休前,我在一家省级党报从事副刊编辑工作。阮道明先生是我们的老作者,几十年来,不管他的工作岗位在基层、机关如何变动,始终都是我们副刊的读、写“铁杆”。
阮先生的作品,充满乡土气息,反映的生活面广,他写乡村、写街市、写年俗、写修身、写养生、写老手艺、写乡之味、写花写树、写山写水、写邑人先贤、写民间传说……无论是童年趣事,还是血脉亲情,或是地方风物,都是那么有新意,有生机,有趣味,有爱心。他真切地感受人生,真实地反映生活,真诚地表达情怀,对于培育他成长的闽山闽水、骨肉至亲,浓墨重彩地倾注了无限的情感和热爱。《银杏王》《儿时的麻笋干》《母亲的斗笠》《满天浮动古馨香》《红色郭婆村》《番薯忆念》《生产队老屋》等等,这些蓄含着特定的文化背景和地域特色的乡土惦念,每一篇都能引起读者共鸣。特别是那些融入对母亲回忆、思念、赞美的篇章,抒发了作者浓厚的心理情感,令人印象深刻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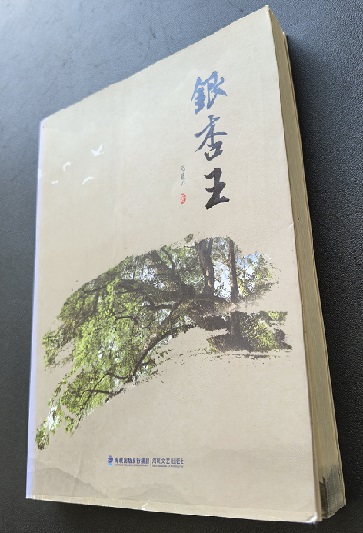

阮道明和他的《银杏王》
在阮先生的多篇散文中,读者都能体会到母亲对他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以及构建。“母亲是位农村妇女,文静清健,善良开朗,乐于助人,因此人缘特别好,村里人都很亲近她”。我们看到,即便是作者辛辛苦苦拾来改善伙食的田螺,母亲也不忘把这来之不易的荤腥美味分享给左邻右舍:“这是我家娃子拾的,有福齐享,大家都尝尝鲜”;在《记忆中的拗九粥》中,母亲在上世纪三年困难时期那种“巧妇难为无米之炊”的窘迫和乐善好施的美德跃然纸上:“拗九粥那天,母亲起得特别早,她用过年做年糕时留开的一点米与野菜混合,煮出了一锅风味迥异的粥。这锅粥虽然‘含金量’不高,但喷香四溢,令人口水直流。我真想先吃为快,可母亲阻止了我,她把粥先敬祖先,再分装在坛罐碗缽中,嘱我分送给里亲外戚的长辈和学校的老师,还有村里的孤寡阿伯阿婆……”母亲心平气和地对一时不解的儿子说:“多碗粥,无非就是多借些米,多采些野菜,无碍事。有我们的热粥,人心不就暖了吗?”
在粒米如珠的饥荒年景里,勤劳的母亲用她的行动和言语,教会了孩子们生活的道理和生存的技能,让他们受益终身。“家里缺乏劳力,母亲为了多挣工分,每日既要为生产队劳动,下了工又要忙家务。她常在劳动休息间隙,在地头田尾割上几把茅草,或拾几根枯木,下工时带回家当柴烧……”母亲的艰辛,孩子们都看在眼里。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,还在上小学的作者,每逢周末或寒暑假,都要脚穿草鞋,身挎柴刀,肩扛“枪担”,上山砍柴。“母亲允许我从中挑出些上等的木柴运到集市上去卖,为自己积攒学费。九岁的我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!尽管幼嫩的双肩磨肿了,手上长茧了,身上伤痕累累,脚趾至今还留下残疾,但我并不感到遗憾。”
“我的斗笠是母亲亲手编织的。编斗笠是母亲最拿手的活。粗糙的手,将绿竹劈开,竹刀掠过竹头竹尾,一以贯之,柔韧的薄薄的篾片,在母亲手上穿梭、跳跃、流连、停驻……”“那个酷暑炎日,我和堂兄去挖薯榔,行走在羊肠小道,老远就被母亲发现了,她在山地打猪草,发现我没戴斗笠,快速过来,摘下头上的斗笠戴在我头上。她说,斗笠是八卦,戴上它,可以御风、避雨、遮阳、祛邪、防害。”作者后来发现,母亲编的斗笠,垫层还夹着蛇药。
作者小学二年级学种番薯,听母亲讲述了番薯的来历和得名,知道了它不怕旱不惧风、喜肥耐瘦的生长习性和优良品质,知晓了乡亲们“爱薯如子”的理由,并从劳动中收获了春夏秋冬的馈赠和感受。当母亲告诉儿子,他断奶后的第一口饭就是泡番薯时,作者感叹:“番薯虽是粗粮,却浸透了母爱”。他在《番薯情结》一文中满怀深情地写道:“我认识了番薯,同时认识了故乡的土地,认识了劳动创造世界的内涵,认识了做人处世的道理。”作者认为,番薯“是影响我一生的精神食粮”。
《挖薯榔》中,母亲挥刀斩毒蛇的果敢和从容不迫的淡定,抚平了小小的作者心中的惊恐畏惧:“别怕!以后接近草丛要用手里的刀或棍子,先来个‘打草惊蛇’,把虫蛇或野兽赶走……”当看到儿子要举斧劈藤,断根挖薯时,母亲极时制止,并给他示范:细心找到主根,然后用山锄小心刨开一面泥土,摘下大块根,整个过程不损坏薯榔的根系与小薯榔,覆盖好泥土,母亲的经验是:“小块薯榔,让它再长,三五年后又有好收成。”并语重心长地告诫儿子:“对人对物,要学会呵护和宽容,凡事不可做绝。”
母亲的勤劳勇敢,聪慧慈悲,在作者的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记忆,以至于在母亲去世几十年之后,每每回想起当时的情景,仍然历历在目:
——困难时期,母亲把儿子带到溪边开垦荒地,教他如何选择地块,才能避免山洪冲刷,她耐心指导,温和调教,告诫儿子:“凡事要防患于未然,考虑周到,才能事半功倍。”;
——《一次难忘的集体年夜饭》里,后厅有母亲忙碌的身影;
——《大年三十卖柴记》中,有母亲殷殷的叮嘱和关怀;
——中秋节,为给卧病在床的父亲买药和饥肠辘辘的孩子们买月饼,有母亲担柴叫卖的辛酸;
……
和善仁慈、温暖静默的母爱,就像阳光雨露,照拂着孩子们成长;她为早早就播下的纯良种子,注入蓬勃的活力,并促其成为后辈不惧风雨、阔步前行的坚强力量;她上下联结,传承庚续,铸就着最纯粹的精神根基。在这生命最坚实的凭依上,作者与母亲血脉相连的情感,延展到与家乡的同休等戚,他对生活有了多重角度的打量。于是,他的作品,眼界更高远了、色彩更丰富了、份量更深重了。
退休前夕,我曾收到阮先生传来的两篇报告文学,一篇是《南极寻梦》,写家乡连江的“渔企”在南极捕捞磷虾的故事,以及对南极磷虾保护、开发和可持续发展的思索;另一篇题为《圆梦大黄鱼》,宣传本土企业家、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和最美科技工作者刘家富的事迹。作者以近八十岁的高龄,深入采访,搜集素材,潜心写作,一遍又一遍地修改完善,那种认真和执著,令人动容!近些年,他热心组织文学采风,把家乡的美丽画卷,满心欢喜地呈现出去。他在用心用情,表达着一位老作家对这片乡土真挚的记挂、感恩和回报。
因为爱,阮先生对母亲充满了无限的眷恋;同样因为爱,阮先生对家乡主动承担起责任。正像他在《其蔬也馥 其蕴也丰》一文表述的一样:“有了这样一种情怀,不管我后来从事什么行业,总把‘责任’二字铭刻心间。还有什么事比身上的责任更重要、更神圣?”
“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,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……”诗人艾青的这行诗句,也是阮先生对家乡的情意和他作品的元气。
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