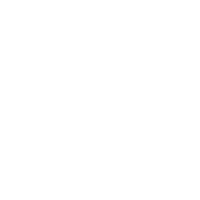渡 塘 火 笼 记
夜深知雪重,时闻折竹声,冬季的第三个节气大雪已来临。忆起小时候的故乡渡塘村,在这个时节是极其寒冷的,雾凇挂满枝,屋檐结冰凌。尤其想起了家乡的火笼。
深冬时节,闽江的水汽到了高海拔的下祝乡便缠绵了起来。这水汽凝成霜,结成霰,薄薄地敷在渡塘村的瓦上、草上、竹叶上。晨起推门,满世界是毛玻璃似的白。风从杉木林、毛竹山的间隙里钻过来,带着山气的寒,直往人骨头缝里钻。那时,火笼便成了我们山乡孩子必备的取暖配套。屋里灶膛的光,成了天地间唯一的暖色。每天凌晨,母亲会从那一团明红里,用火钳小心地夹出烧得正透的火炭,妥帖地安放在火笼圆肚的土陶碗里,上面匀匀地撒一层灰白的柴灰,备着给要起床的孩子们。

我们家的火笼大多是洋边村佑爿亲家翁编的。渡塘村后山多的是毛竹,亲家翁选的是背阴处长了三年的老竹。他说,向阳的毛竹性子躁,易裂;背阴的竹,吸足了地气的寒润,有韧性,经得起岁月的盘弄。篾刀在他手里象听话的玩偶,破竹,削篾,青黄两层细细分开。青篾硬朗,做骨架;黄篾柔顺,便一圈圈绕着骨架编织。他的手指肥硕粗短,布满老茧,可那竹篾在他的指尖里却像流水一般柔顺,交错回环,最后收口成一个浑圆的鼓肚。那纹路如一个个小菱花,挨挨挤挤,密不透风。最后一道工序,是将那煅烧过的土陶碗放进鼓肚里,严丝合缝,再用篾丝编织成圆筒底座,一个崭新的火笼便成了。

上学的时候,我们背着书包,提着火笼,走在青石板与黄土夹杂的村径上,嘻嘻哈哈地向学堂走去。路旁的狗尾草挂着霜,硬撅撅的,我们用火笼轻轻一靠,霜便化了,留下一小圈濡湿的暗色。有时贪玩,从火笼里拨出一块红炭,放在路旁沟洼结冰的冰面上,看它“滋”地一声,冒起一缕几乎看不见的白烟,竟也觉得十分有趣。
那时渡塘村的学堂,学风鼎盛,教学水平在乡里名列前茅,还兼办着初中一年级。周边的汶洋村、邹洋村的孩子都在渡塘上学。新建的校舍在村东头花瓣坵发小马汉鸿家的前面,容不下这么多人数,小学一二年级就借设在旁边华仕伯的老房子里。风从雕花的木窗棂和空旷的天井自由出入。先生讲“冰雪融化,种子发芽,果树开花”,声音洪亮,可我们藏在课桌下的脚,却冻得像是别人的,不停地互相磕碰着取暖。于是,火笼便从家里,蔓延到了课堂。那时没有电,房间改成的教室光线昏昏的,二三十个小小的火笼,便在桌下、在脚边,亮着幽幽的红光。炭火的气息,混合着旧书页的霉味、还有某个汗脚同学的袜子烘烤出的难闻气味,酿成一种独特而习惯的味道。那是贫穷岁月里,我们自己给自己点起的小小太阳。
火笼里的炭,是有生命的,需得人时时照看。上到第二节课,那股暖劲儿便有些衰了。这时,便悄悄从铅笔盒里抽出半截竹尺,探进去,轻轻拨弄。将四周那些烧乏了的、蒙着白灰的炭,拨到中间那点红心上。只消一会儿,那红心便像醒了过来,重新焕出光彩,暖意又丝丝缕缕地透上来。也有窘迫的时候,家里的炭火没接上,带出来的火笼,半路就“睡”着了。只好臊着脸,将冰凉的脚,悄悄挨近同桌的火笼。他若不声张,便是默许了这份共患难的暖意。那种时刻,无需言语,一种粗朴的、属于孩童的仗义,便在那微红的光晕里传递开来。
火笼的妙处,远不止于暖手暖脚。冬日漫长,肚子里油水寡淡。不知是谁先开的头,竟发现了火笼另一好处。从家里偷出拇指大小的一截红薯,或是几粒黄豆,趁先生转身板书的当口,飞快地埋进炭灰里。那等待的时光便有了焦灼的甜蜜。红薯的香,是缠绵的,一丝丝,一缕缕,顽强地从竹篾的缝隙里钻出来,勾得人魂不守舍。待到下课,急急地刨出来,红薯已变得稀软,烫得在两手间颠来倒去,小心地撕开一点皮,金黄的瓤子冒着热气,一口下去,那股滚烫的甜,能一直落到胃里,仿佛把整个冬天的寒气都驱散了。吃黄豆更需技巧,用空的“百雀羚”或“万紫千红”润肤脂的铁盒子装上黄豆埋入火笼的炭火里,听得炭灰里有“啪”一声轻响,便要眼疾手快地夹出来,丢在地上冷却,揭盖争食,酥脆焦香。有时嘴角常因此留下一点黑灰,互相指着,笑得前仰后合,常被先生逮着罚站。

夜幕落下,火笼的角色便从学堂转回家庭。昏黄的油灯下,它成了一家人无声的陪伴。奢侈的享受在睡前,母亲会将火笼放进被窝深处,先暧烫一会儿。等我们钻进去时,被窝不再是冰窖,而是像晒了一整日太阳的稻草堆,干燥蓬松,散发着阳光与烟火混合的、令人暖心的气息。身子蜷进去,听着窗外北风掠过竹梢的呜咽,觉得那风再大,也吹不透这一床用火笼熨帖过的温暖了。也有乐极生悲的时候。村里老叔公贪暖,将火笼直接塞进脚头,酣睡至半夜,梦中只觉得脚底板热得发烫,惊醒一看,袜子和棉褥已烧出一个焦黄的洞,兀自冒着丝丝青烟。此事成为村中笑谈许久,却也无人真正责怪。
后来,我像许多村里的年轻人一样,沿着那条走出山的古道,越走越远。城里的冬天,是靠空调与暖气片抵御的。恒温,稳定,洁净得没有一丝烟火气。暖手宝做得精巧可爱,充电即热,却总觉那热浮在表面,像一层塑料薄膜,隔着了什么。童年那抱着火笼、踏着霜雪去学堂的日子,蜷在火笼熨热的被窝里听风声的日子,遥远得像一个泛黄的梦。
前几日回村,看着一幢幢熟悉的老屋已人去屋空,颓垣断壁,曾经辉煌的学堂也已颓败不堪。正怅然间,忽见村部的墙根下,坐着两三位老人,穿着厚厚的衣裤,每人怀里,竟都还搂着一个火笼。竹篾已被岁月摩挲成深沉的紫褐色,油光发亮,如古铜一般。他们沉默地坐着,间或低声交谈两句,枣皮似的脸上皱纹舒展。阳光淡淡地照着,他们怀里的那一点微红,在萧索的冬日背景下,显得如此笃定,如此安宁。
我忽然怔住了。那一刻,穿过数十年的光阴,我仿佛又变成了那个抱着火笼、走在上学路上的孩童,感受到那火笼里的炭火安静持久的呼吸。那是来自山林深处的竹木交织的温暖,在漫长的岁月里,仍然不疾不徐地烘燃着,驱散了物质的贫瘠与自然的严寒,最终将一种沉静的底气,烙进了一个山乡孩子的骨血里。
如今的取暖之物,林林总总,高效便捷。可没有一样,能如渡塘的火笼这般温暖,将天地的生息、人手的温度、岁月的深情,含蓄又丰沛地编织在一起,展现在你眼前。
我忽然觉得,它已不是火笼本身,是那些在寒风中曾紧紧相依的、再也回不去的时光。火笼土陶碗里柴灰覆盖下的故乡炭火,那一点红心,从未真正熄灭过。